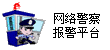知青的那一年,鬼使神差的我竟向队长要求去养猪。众所周知,养猪是个既脏又累的苦差事,我这个匪夷所思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满足。旋即,“小猪倌”走马上阵,开始我知青生涯中的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。
养猪,最大的困难的喂猪。其难在不是如何喂,而是喂什么。那是个物质缺乏的年代。
起初几个月还好。我们的生产队旁有一条小河,依据有利地形修了一个小水电站,因而就有动力装了一台小碾米机为当地农民碾米,以他们的米糠作为补偿而免交任何费用。于是,我每天早上开工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两个麻袋去收米糠。当我挑着几十甚至上百斤沉甸甸的担子往回走的时候,尽管头发上都沾满黄澄澄的糠末,衣服上一片“黄尘”,浑身上下除了眼睛黑的牙齿白的之外,真正一个“黄”种人了。虽然头上的汗水淋漓,脸上开出条条“运河”,一张名副其实的大花脸,但心里甜滋滋的,那些猪有吃的啊。那段日子虽辛苦,但猪养得还似个猪样,心里还是有点高兴的。
可惜好景不长。很快,小水电站划归农村公社所有,不仅免费的米糠没了,连买都没地方,猪猡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们是国营农场,每个月国家配给每个人四十斤大米,在那时,缺油少肉,甚至连青菜都是希罕品,我们干的是重体力劳动,不要说四十斤,六十斤也吃得完,我每天从饭堂的洗米水中也难得淘出一粒米花。
如果运气好一点,碰上生产队或附近农民收地瓜,就去检些瓜滕回来剁碎煮熟,掺上洗米水,饿极了的猪吃得挺欢,应付上一阵子。大部分时间只靠挑着个空担子,漫山遍野的逛,看哪里有无毒的野草就割它一担回来。实在没办法,就冒着被重达二两的热带水蚂蝗放血的巨大危险,下到水深过膝的小水塘里捞水浮莲。回来后就用当时最盛行的办法,下些曲种与剁碎的水浮莲拌匀,封进大水缸里发酵,数天后取出就是猪们的“佳肴”。这等食物不仅营养价值低,且口感差,猪极不爱吃,身体迅速消瘦,各种疾病随之而来,只好死给你看。我每隔三五天,就要给他们其中之一举行一次告别仪式,在林段里掘一个洞,放好它们的遗体,培上土,然后双手合十,嘴里念念有词,向上天祷告,愿它们在上天能吃上一顿饱的。最惨的一次,从场部猪场拉回六十只活蹦乱跳的猪苗,最后成活的不到五只。在那个天天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颠倒的日子里,人都没吃的,何况是猪!要怨只能怨它们赶上了那个时代。
但也有一些特别厉害的猪,在如此的炼狱中竟然练出一身好本领,身轻如燕,一蹦一米多高,从猪栏爬出来到外面觅食。那些零星散布的野菜、土里的蚯蚓、橡胶工人割出来的胶水都成了它们的口中之食。毫无疑问,这些猪都活下来了。
那时的猪有几个特点:嘴尖,毛长,背薄,身轻。乍一看,就是一群山猪!吃胶水的猪还多了一条黑乎乎的“尾巴”(胶水在猪胃里凝结成胶块,不能消化,又从肛门排出,成一长条,吊在屁股后),晃来荡去,令人哭笑不得。
从猪圈里逃出来的猪是国家财产,在我的脑瓜中,国家财产高于一切,无论怎样最终还是要将它们“捉拿归巢”。这些猪在外面找到一些吃的,又长着四条腿,跑得够快,两条腿的人追它谈何容易。起初,我见到一只就追一只,看到两只就追一双。拼上老命死追,虽然猪是捉到了,人也大汗淋漓,气喘吁吁,隔夜风炉也吹得着。
后来追得多了,看出了一点门道:那些猪们虽长着四条腿,有着先天优势。但长着一个猪的蠢脑袋。它一被人追,只会撒开四蹄没命的逃,而坚持不了多久,不到十分钟就没气了,当它发出绝命的嚎叫时,就是告诉你,它不行了。这个时候你抓它,轻易可将它扳倒,甚且连挣扎都没力气了。从此,人们经常看到我在林段里跟在逃猪的后面长跑,直到猪发出绝命大叫时,我才出手把它摁倒在地,然后提回猪栏,真是事半功倍。
有一次台风过后,猪栏边的小河涨大水,混浊的黄汤几乎与河岸齐平。我追的那条猪居然慌不择路,一直朝河边奔去。我心中暗喜:哈哈!前边浊浪滚滚,看你往哪里跑?到了河边,只见那猪毫不犹豫,扑通一声就往水里跳,迎着风浪,划动四蹄向对岸游去。当时真是我意料之外,这家伙真玩命了!我要不下水真辱没了出自游泳队的英名。随即我也跳下水,与它进行水中竞赛。到了对岸边,它呼拉一声蹿了上去,继续再跑。我紧跟着。不一会儿,那猪嗷嗷大叫,跑不动了。这时我才出手将它擒拿
平平淡淡的养猪日子在脏臭和艰苦中流逝,但有一次,我差点淹死了一头大水牛。
那天,生产队里收地瓜,我套上一辆牛车,赶去拉瓜藤回来当猪饲料。时近傍晚,满满的一车瓜藤有一人多高。我在前,牛在后,牵着牛乐悠悠的往回走。到了小河边,眼看猪栏在望,心也放松了许多。几十米宽的河上的桥是用手臂般粗的小树干在水里打桩成桥墩,上铺二十来公分宽的小树干做成的简易桥,人在桥上过,简直像走平衡木,时刻平衡着身体才不致于掉到水里。我按照惯例,人在桥上走,牛拖着车从水里游过去。因为车重,瓜藤堆得又高,牛下水前我还特意用绳子把牛轭绑死,免得在水中脱掉,一车瓜藤付水东流。
到了河中间,一个不留神,牛绳被桥桩挂住了,往左拉牛鼻子。水牛以为我发出左转的命令,马上向左拐直钻桥孔。这一下就坏了,高耸的牛车即时翻转,连带着牛轭把牛也反转过来。只见牛头被牛车臂压进水里,呛着水,咕咚咕咚的喝着,四脚乱舞,眼看就要沉入水中,一场淹死水牛惨剧就要发生。说时迟那时快,见势不妙的我马上跳下水中,拔出别在身后的海南砍刀拼命把绑着牛轭的绳子砍断,挣扎的牛脚好几次差点踢到我的肚子,要是踢中的话,肚子也要开花。牛松去了束缚,立马浮上水面,打着响鼻,缓缓游上岸,一车瓜藤顺着河水流向下流。我爬上岸,周身湿淋淋的,抹去脸上的水和汗,惊魂未定。心想,要是这出戏做成,我不知要犯下什么弥天大罪,成为当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。真是老天有眼!
城里学生哥养猪,在现代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。它苦在哪里,脏在何方,不亲身经历,有时还说不清楚。
首先,累。那时,每天都要挑沉重的担子。或是一百几十斤重的米糠,或是爬山涉水找猪菜,还有每天挑猪食喂猪,挑水洗猪栏等,全都离不开四尺扁担。对于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娇生惯养学生哥,开头的日子一拿起扁担心里就发麻,沉重的担子压得肩膀发痛,双腿颤抖,步履蹒跚,呲牙咧嘴,辛苦异常。不多久,肩头上挑得隆起一块肉,死实死实的,几乎针扎也不觉得疼。当时有毛泽东思想做精神支柱,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作偶像,硬是撑了过来。但有些人就没这么好彩了,繁重的体力劳动给他们落下了一身病。我有两个朋友就是如此,至今没有成家。其中一个两边股骨头严重磨损,须换上人工关节才能走动。
其次,脏。养猪离不开与猪屎猪尿打交道,每天必须挑水洗猪栏。猪栏靠近小河边,用水必须下河,挑水无法穿水鞋,只有光脚或穿塑料凉鞋。猪屎臭不必说,顶不顺的话戴个口罩之类还可有点用处,但对那双脚就麻烦大了。经常接触猪屎猪尿,脚丫被腌烂,不仅臭味洗不清,晚上还直痒得睡不着。实在忍不住,只能搽碘酒止痒,痛得直抽冷气。我因此又感染了当地的钩端罗旋体病原虫,酿成了日后一场大病。此外,天天接触潲水,双手的那股下多少肥皂也洗不掉的味道令人吃饭时总觉恶心。当时的我,穿着一条球裤,腰缠一条吸汗的毛巾,皮肤黝黑(光着膀子被太阳晒的),两眼发光(戴着眼镜),身上散发出一股猪臭味,就是一时代老农!
再就是苦。生活艰苦,思想苦闷。那时所有的知青都一样了。空有报国之心,却报国无门;想要读书,却求学无路。每天披星戴月,干着重体力活。与其美名曰接受再教育,不如说是流放天涯海角改造。那时,天天早请示,晚汇报,饭前做祷告;背语录,跳忠舞,晚上听报告。斗私心,挖修根,受老农“教导”;吃白饭,无肉菜,心怀世界浩。肉体折磨,思想压抑,看不到前途,望不见曙光。自己苦不堪言,还深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活在水深火热之中;自己生活艰难,还气高志远,要去解放全人类。现回想起来,何止幼稚荒唐,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!我们一代人,几乎成了政治战场的工具和牺牲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