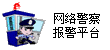我在麻木不仁的夜班和白班之间游弋,变成了生活的囚徒。掐指数来,已两年半没出过差了,正好有个任务是去厦门招人,我眉开眼笑,抛妻别子,以放生的姿态朝鼓浪屿咆哮而去。
再次望见闽地的灯火,心有唏嘘。21年前第一次进入福建,我一脸傻逼,头上顶一颗大痣,是看个三级片都会脊背冒汗的乡下少年。如今胖了30斤,头上的痣也没了,成了一刀疤男。当夜和厦门的大学同学饮 得烂醉。我们都已来来 人世的正午,都是为生计奔忙的中年。当公安局长的哥们去浙江追逃了,缺席;当钱庄老板的哥们割掉胆了,拒绝跟我拼酒;当银行行长的哥们,准备派驻南非数年,正愁眉彷徨间,大家却嚷着叫他夹带些钻石和黄金归回,他说这玩意没法入关,大家说藏于直肠里可径直通关,我沉吟良久,说,倘还有间隙 ,我想劳烦你……带一根象牙归回。
醒来摇摇摆晃去厦大,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妹子排成了长队,我掐了一把大腿当然是自己的才确信这不是在梦中。我打醒精神,以免自己把“林昆”叫成“木棍”,这是极可能的,林是福建大姓。一路聊去,忽然很伤心 。学新闻的孩子说不出一个晓 名记者的名字,自称写现代诗的文青除了舒婷外谁都不晓 道,中国养猪网,学历史的硕士说国民党勾结日寇所以最终败走大陆。还有个姑娘自称最爱看的报刊是《看天下》,我深情地让她说几个喜爱的作者名字,那一霎心想只要她说出宋石男谭伯牛的名字,我就让她直接进入笔试,若是竟然说出“刘原”,我就叫她收拾细软跟我归长沙,结果妹佗嘻嘻笑着,说一个都记不住。
我边刻薄地问刁钻的问题,边真诚地给这些孩子提建议,教他们该读什么报刊,该准备什么样的简历。终究食 过四年福建大米,对闽地的孩子还是有感情的。新闻虽是苦活,但也是有技术门槛的,哪怕去当人蛇也得先学会洗碗。我的唠叨并不属于面试官的职责,只是想起了自己和他们一样青春的时候,那些凄惶的求职岁月。
收工后,直奔南普陀。在峰顶望见金门渺茫,想起林志玲正日复一日老去,心中一痛,下得山来,在庙墙上看来 李叔同临终手书的“悲欣交集”,心里又是一痛。我当年被福建的大学充军贩卖来 荒凉的水电站,如今又来来 福建的大学贩卖人口,内心是有悲欣翻动的。
入夜惯例群醉。说起前尘,都觉得少时找工作的难度,和中年艰辛不能比。有哥们从公务员来 倒爷来 记者什么都干过,现在正养兔子。还有个哥们在东莞混迹多年后,归厦门放贷,事业大不如前,因为当年他在东莞每夜都放出几个亿。我说,有梦想即可,你们看电视上的冰壶比赛,那些猛挈 地板的都能挈 出个世界冠军。说这话时,鼓浪屿上空的明月升起来,像一桶水银浇在了我们的白头,或者秃头之上。